期刊VIP學(xué)術(shù)指導(dǎo) 符合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zhì) 保證專業(yè),沒有后顧之憂
期刊VIP學(xué)術(shù)指導(dǎo) 符合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zhì) 保證專業(yè),沒有后顧之憂
來源:期刊VIP網(wǎng)所屬分類:漢語言時間:瀏覽:次
摘要: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是村民日常生產(chǎn)和交往過程中形成的精神文化生活場域,是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生活的空間表達形態(tài),集中體現(xiàn)了村民的文化價值取向。在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重構(gòu)路徑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wù)是由外而內(nèi)的最全面引領(lǐng);培養(yǎng)文化自覺是由內(nèi)而外的最根本途徑;重拾文化記憶、凝練文化空間特色是生命力的源泉。以滿足村民日益多樣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為價值取向,從空間重構(gòu)的角度對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的變遷進行研究,能夠拓寬當(dāng)代鄉(xiāng)村振興發(fā)展的基本思路。
關(guān)鍵詞:鄉(xiāng)村振興;公共文化空間;文化記憶;空間重構(gò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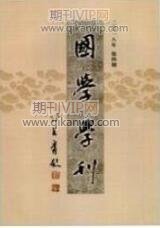
在鄉(xiāng)村振興倡議提出的背景下,全方位地促進鄉(xiāng)村振興倡議的實施,從制度、經(jīng)濟、文化、生態(tài)等方面轉(zhuǎn)變鄉(xiāng)村的發(fā)展方向,推動鄉(xiāng)村全面振興的實現(xiàn)成為新時代鄉(xiāng)村發(fā)展的重要內(nèi)容。習(xí)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diào),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務(wù)體系,深入實施文化惠民工程,豐富群眾性文化活動①,而鄉(xiāng)村文化建設(shè)在整個倡議實施中具有重要地位。作為鄉(xiāng)村中最為典型的內(nèi)在精神表達,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無疑是鄉(xiāng)村振興倡議的助燃劑,而公共文化空間作為鄉(xiāng)村文化的承載體,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發(fā)生了從內(nèi)容到形式的流變。為了更好地適應(yīng)人民對多元精神文化的需求,對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的重構(gòu)成為必然趨勢。
一、建構(gòu)與解構(gòu):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實踐表達
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是鄉(xiāng)村文化鮮活的載體,是村莊歷史文化積淀和村民日常生活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公共場域,是村民精神文化的集中體現(xiàn)。農(nóng)村公共文化空間,是一個既包括農(nóng)村文化生活所依托的物理場域,又涵蓋文化資源、文化活動和文化機制在內(nèi)的整體性概念②。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是在長久的歷史流變過程中建構(gòu)起來的,與鄉(xiāng)村的發(fā)展歷史緊密相關(guān)。在鄉(xiāng)村振興倡議實施的時代背景下,完善農(nóng)村公共文化服務(wù)體系,發(fā)展農(nóng)村公共文化服務(wù)成為了重要任務(wù)。
(一)鄉(xiāng)村文化的“都市想象”
城市和鄉(xiāng)村并不是一個對立面。鄉(xiāng)村這一概念的提出有別于農(nóng)村一詞,農(nóng)村是單純地從經(jīng)濟角度與城市劃分區(qū)別,而鄉(xiāng)村則更多的是從地域和空間的角度進行的劃分。黨的十九大提出要按照“產(chǎn)業(yè)興旺、生態(tài)宜居、鄉(xiāng)風(fēng)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體要求實現(xiàn)鄉(xiāng)村全面振興,而鄉(xiāng)村振興的過程就是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重構(gòu)的過程。長久以來,鄉(xiāng)村空間一直被定位為城市發(fā)展的資源性補給站,鄉(xiāng)村自身空間的發(fā)展被忽略,造成大量資源的流失和消逝,進而導(dǎo)致城鄉(xiāng)差距不斷擴大。隨著新型城鎮(zhèn)化的快速發(fā)展,有一部分村民已經(jīng)走出了鄉(xiāng)村,成為了新型城鎮(zhèn)化的生力軍。對于他們來說,與其說城市是相對于鄉(xiāng)村發(fā)展起來的,不如說鄉(xiāng)村是相對于城市而存在的。城市是基礎(chǔ)設(shè)施、文化娛樂、經(jīng)濟基礎(chǔ)、人文環(huán)境、社會組織等都相對完善的空間,文化空間也更為豐富和多元。成功走出去的生力軍們進入到城市感受到了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活力,回到曾經(jīng)賴以生存的鄉(xiāng)村,就不自覺地成為了耳濡目染的城市文化的傳播使者,成為了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建構(gòu)的引領(lǐng)者。社會組織結(jié)構(gòu)的完備給城市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魅力面紗,讓生活在鄉(xiāng)村的人們對其充滿了想象和神往,努力地想要成為城市的影子,以縮小城鄉(xiāng)差距,正是這樣的“欲望追求”才使得新型城鎮(zhèn)化有了快速發(fā)展的可能。在這樣的背景下,現(xiàn)代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建構(gòu)必然透露著都市的色彩,充滿著村民們的都市想象。但因為建構(gòu)過程的獨特性和村民與文化空間的有效互動,使得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又是一個有別于城市文化空間的獨立存在,有其自身的發(fā)展邏輯。村民是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中相對固定但又不穩(wěn)定的因素,村民個體的獨特性對公共文化空間的建構(gòu)有不言而喻的催化作用。完成對鄉(xiāng)村“都市想象化”改造的最原始動力就是村民對都市文化的自覺認(rèn)同,但在這一過程中,對鄉(xiāng)村原生態(tài)文化的尊重是與一切他者文化融合發(fā)展的基礎(chǔ),文化的在地性發(fā)展是保障文化健康良性發(fā)展的根本。
(二)文化記憶的“朝花夕拾”
記憶是闡釋空間和地方性意義的組成部分,并對地方的認(rèn)同產(chǎn)生重要影響③。文化記憶是鄉(xiāng)愁的凝練。揚·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記憶的概念,這在人地關(guān)系發(fā)展急劇變化導(dǎo)致鄉(xiāng)村文化記憶逐漸沒落的當(dāng)下有著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記憶和鄉(xiāng)愁所依附的城鄉(xiāng)空間,是其賴以延續(xù)和發(fā)展的物質(zhì)載體④。文化記憶是建立在群體記憶基礎(chǔ)之上的,在代際交流中逐漸形成范本,并發(fā)生著流變。這一文化空間內(nèi)的群體對空間內(nèi)的文化記憶有著高度的認(rèn)同感和文化自覺,因此文化記憶具有穩(wěn)定性,不會輕易地隨著代際交流主體的更替而消逝。鄉(xiāng)村文化記憶空間是具體的記錄、承載和展示鄉(xiāng)村文化記憶的特定場所,它不僅是鄉(xiāng)村文化產(chǎn)生、發(fā)展和延續(xù)的空間載體,也是鄉(xiāng)村地方身份認(rèn)同、鄉(xiāng)村旅游價值展示和地方場所精神再現(xiàn)的重要組成部分⑤。新型城鎮(zhèn)化帶來了許多城市人的“都市綜合征”,繁冗的工作讓人滿心疲憊,快節(jié)奏的生活壓力促使人們想要逃離,鄉(xiāng)村的文化記憶在這時被激活重拾。為了迎合都市人休閑的生活理念,在原有的鄉(xiāng)村社會框架基礎(chǔ)之上,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符合都市情感認(rèn)同、體現(xiàn)鄉(xiāng)村文化延續(xù)、反映社會發(fā)展傾向的文化識別符號集合被建構(gòu)起來。
二、根源與沖突: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重構(gòu)的原因及問題
鄉(xiāng)村文化空間是與村民休戚相關(guān)的主要生活空間,風(fēng)俗習(xí)慣和地域文化造就了特色的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這個文化空間反過來又會影響村民人生價值觀、道德情操和人文素養(yǎng)的養(yǎng)成。法國哲學(xué)家列斐伏爾說過,如果未曾生產(chǎn)一個合適的空間,那么“改變生活方式”和“改變社會”等都是空話⑥。由此可見鄉(xiāng)村的全面振興必然是生活方式和鄉(xiāng)村社會的雙重改變。
(一)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重構(gòu)的原因
1. 鄉(xiāng)愁的“無處安放”
鄉(xiāng)村是多數(shù)人的情感歸宿,鄉(xiāng)村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根本,是中國的根脈。城市文化空間是鄉(xiāng)村文化空間的延展和升級。新型城鎮(zhèn)化的快速發(fā)展加快了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的進一步失衡,人員流動成本的降低促進了大量外來人員涌入城市,但是鄉(xiāng)村文化的烙印卻始終印刻在這些“外鄉(xiāng)人”身上。鄉(xiāng)土文化和都市文化形成了交織,兩者間的博弈造成了人們自身文化場域的力量失衡,產(chǎn)生了“無處安放”的鄉(xiāng)愁。習(xí)近平同志說“要記得住鄉(xiāng)愁”,鄉(xiāng)愁是鄉(xiāng)村文化記憶深層次的精神映射,是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現(xiàn)代建構(gòu)中重要的文脈支撐和靈感源泉。鄉(xiāng)愁是鄉(xiāng)村文化“重生”的動力,“鄉(xiāng)愁力量”成為新時代的生產(chǎn)力。文化記憶是由特定的社會機構(gòu)借助文字、圖畫、紀(jì)念碑、博物館、節(jié)日、儀式等形式創(chuàng)建的記憶,它具有特定的載體、固定的形態(tài)和豐富的象征意義⑦。鄉(xiāng)村文化記憶的體驗就是鄉(xiāng)愁實踐性的表達,民眾在對鄉(xiāng)村文化記憶的體驗中尋求鄉(xiāng)愁的回歸。對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建構(gòu)不僅要從鄉(xiāng)村自身的公共文化服務(wù)角度出發(fā),還要向外尋求與文化消費市場的契合。尤其是在一些古村落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中,旅游市場成為了發(fā)展的契機。文化消費旅游的最終目的是對文化的消費和對文化記憶的追尋。“只有在某人的形象喚起了我們的回憶和感情的時候,我們才會愿意去了解他的行為舉止。”⑧ 記憶不斷經(jīng)歷著重構(gòu),過去在記憶中不能保留其本來面目,持續(xù)向前的當(dāng)下生產(chǎn)出不斷變化的參照框架,過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斷重新組織,也就是說,記憶不僅重構(gòu)著過去,而且組織著當(dāng)下和未來的經(jīng)驗⑨。在這一組織框架下,對文化記憶的凝練、表達與重構(gòu)就是對鄉(xiāng)愁的再定義,它構(gòu)成了鄉(xiāng)村文化體驗空間建構(gòu)的基礎(chǔ),并表現(xiàn)出連貫性和持續(xù)性。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就是喚醒文化記憶的“培養(yǎng)皿”,鄉(xiāng)愁的“無處安放”從根源上推動了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的重構(gòu)。